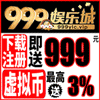话说河南彰德府安阳县有个秀才,姓刘名玉,发妻袁氏,乃元宵所生,唤名元娘,夫妻二人如鱼似水,家中奴仆成行,牛羊成队,说不尽金玉满堂。
后边一个花园,也是天上有,地下无的,名曰日宜园。各样各花,都不说起,单说他家牡丹花,比别家不同,乃是河南专有好种。
一到季春,牡丹盛开,他便请了亲朋邻友,赏玩,吟诗,作赋,好不有趣。
其时三月初旬,牡丹比往年又盛了几分。刘玉先与元娘置酒庆赏,但见茂郁非常,盆旋翔舞,如喜若狂。
刘玉道:“莫非花神至?”
元娘见说,把酒浇奠拜下:“花神有灵,秋间再发。”
刘玉笑道:“那有一年两放的花。”
元娘道:“岂不闻武后藉春三日?那也是秋天,百花争放,牡丹先开,故封他为花王。岂不是一年两次开花广刘玉道:“他是一朝武后,故此灵验。”
元娘道:“怕古诚则灵,我一念至诚,倘然灵起来,也未可知。”
那花烁烁的动了几动,元娘道:“你看,岂非花神有灵。又没有风,这般摆动。”
刘玉看见,也自惊起来,连忙将酒拜祭。
那夏天已过,秋色来临,绕见桂蕊飘香,又有东篱结彩。
这秋色虽不能如春天百花烂漫,然而亦不减于春也。
夫妻二人阔步往从牡丹台走过,刘玉道:“秋色已到,牡丹不开了。”
元娘道:“只好取笑而已,世间那有此事。”
偶尔上前一看,夫妻二人大惊道:“奇了,莫非眼花,为何花都将笑了。”
元娘道:“难道我二人俱眼花不成。”
唤些使女们来看,只见来了几个使女,都惊道:“果是花将开放。”
喜得刘玉夫妻双双拜下道:“花神,你如此有灵有信,我刘玉夫妻好生侥幸也。”
分付小使,点起香烛,置酒果拜祷了一番。便道:“春间赏花的亲友许我说,如秋间开花,他们置酒作东。待花盛了,不兔写着传帖,约他们来看。”
且说河南南阳府镇平县,有一个百万家财的监生,姓蒋名青,年纪二十五岁了,往省城寻亲而回,过经安阳县,闻说牡丹盛开,他满心欢喜,有这样异事,怎不一看。
乘了轿子,跟随了几个家人,一路上挨挨挤挤,到了刘家园门下轿,挤进里边。
蒋青见了牡丹十分啧啧。 头周围一看,恰好看见了前世冤家。
他眼也不转,看着元娘。越看越有趣,正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那元娘在楼上与几个女伴调笑自如,果然雅趣,并不知有人偷看。
这蒋青看之不了,只顾站着,家人道:“相公,回寓所去罢。这花不过如是了。”
蒋育说:“我在此看着花娘哩。”
家人不解道:“轿夫腹中饥了,要回去吃饭。”
蒋青无奈,只得走出了园门,与一心腹家人,唤名三才道:“你可在此细细打听园主姓名,年纪多少,并妻房名氏。方才楼上穿白纱的妇人名姓,快来与我说,不可记差了。”
三才道:“理会得。”
蒋青上轿去了。
那三才往邻居问了,又向邻家去问,又如此说,问得仔细,回着主人道:“花园主人名唤刘玉,年方二十二岁,本县学里秀才。那白纱袄的妇人,正是他的妻子。姓袁,父亲兄弟,都是秀才。妇人幼名元娘,家中巨万家私。礼贤好客,良善人家。”
蒋青听了,说道:“好气闷人也。”三才道:“官人家中钱过北斗,莫非没有这般秋发名花,所以如此气闷?”
蒋青道:“你这俗子,我爱他元娘,真如解语之花。无计可施,所以气闷。”
三才道:“官人在家时,事事都成。为何这些计较便无了。”
蒋青道:“谋妇人,与别事不同。如嫁之夫,或是俗子,或是贫穷,或是年老,或是俭涩,或是丑貌,诸事得一,便可图之。今观名花满园不俗可知﹔巨万家财,不穷可知﹔年方念二,不老可知﹔礼贤好客,不涩可知﹔秀士青年,不丑可知。无计可施,自然气闷。”
三才道:“官人,小人倒有计在此。”
蒋青道:“若有计,事成自然重赏。”
三才说:“官人,事成不敢求赏,事不成不可赐责,官人目下回家,离此有半月之程。况又是自家船只,将行李收拾完备。我们大小跟随之人,有二十余个在此。到更深之际,单单只抢了元娘,一溜风走他娘。除非是千里眼看得见。不知官人意下如何?”
蒋青道:“此计倒也使得。恐一时难进去。”
三才道:“不难,正好把看花为名。傍着天色晚来光景,一个个藏在假山之后。鬼神也看不见。”
蒋背道:“不须用着枪刀。”
三才道:“尽多在此。一个人一把刀,或是一柄斧就够了。面也不须搽得。只是一件倒难。”
蒋青道:“是何物件?”三才道:“半夜三更,须得些火把方好。倘然黑麻麻的,元娘躲过了,抱了一个老婆子来,可不扫兴。”
蒋青道:“这也不难。一个人一条火把,笼在袖中,带了火草,临期点起便是。虽然如此,不可造次。今夜你可先去试一试,何处可以藏人,何处人内,何处出门,有些熟路方可。如此万一被他拿住,如之奈何?”
三才道:“说不得了。吃黑饭,护兵主。我去我去。”
蒋青赏了他三钱银子买酒吃。待后又有稿赏。
三才领了银子,与同伴几个人,同往酒肆中,吃得醉醉的,归家与主人说了,竟自往刘国而来。
一路上只听得说刘家牡丹花开得奇异,有的说庭前生卉草,总好不如无。
三才听见这两句说话,便道是真话,说得有理,閑话之间己到门首。他挤进园门,竟至牡丹后面去。
看那园十分宽敞,往假山上面一看,其间山洞中,尽好藏身,且是曲折得很。
又往园一看,此处可至内室,有门不闭,他使握将进去,不见一人。
原来刘家男妇,俱在这些花园,看着人往人来,况前门已是拴好的,故此无一个在内室里。
三才不见有人,又往楼上一望,想道,毕竟也无人在上面。
轻轻的上了楼梯,知是主人的卧室,往窗外一看,只听得花园内沸腾腾的人声。
他便走到床上一看,见枕头边有一双大红软底的大睡鞋,只好三寸儿长,他便袖了流水的下了楼来,又往原路几走了出来。
只听得有人说:“这花虽好,明朝一日也都谢了。”
三才思道:“此事只在明夜了。”
回见主人,将前事一说,蒋青大喜:“事倘成时,你功第一。只是一件,这样一个标致妇人,倘然一双大脚,可不扫兴了蒋青也。”
三才道:“官人,若是一双小脚,还是怎幺?”
蒋青道:“若是果然小脚,赏你一百两银子。”
三才道:“只要五十两,快快兑来。”
蒋青道:“敢是你先见了。”
三才说:“官人,若要看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便是。”
蒋青道:“蠢才,终不然你割了她那一双脚来不成。”
三才往袖里一摸,将那鏽鞋摆在主人面前。
蒋青一见,拿在手中,将双脚平跌道:“妙,妙,足值一千两银子。”
三才道:“五十两还不肯赏哩。”
蒋青说道:“决然重赏。”
拿在手中,如掌上珠一般,何曾释手。
三才道:“今晚各人早睡。明日就要行事。若再迟,花谢了,闭了园门,做梦也不得进去了。”
蒋青分付众人,与五钱银子买酒吃,明日齐心协力,事成之后,自有重赏。
众人欢天喜地,应了一声,都去吃酒去了。
蒋青自己一个,自饮自斟,把盏儿放在鞋儿里,吃了又看,看了又吃,直至更尽,把鞋儿放在枕边而睡。
到次早,先自起来,分讨把行李收拾下船,连人都下船里去,把寓所出还了主人,三才去买了火把,收拾器械,大家煮饭吃饱了,俱随着三才而去,止留下一个小使伏侍主人。
三才到了彼处,一个个的领进假山洞里,安顿停当,自己又往昨日那门边了看一了会,天色晚将下来,游人散了,花已凋谢,亲友也不来夜间赏了,故此刘玉着小使闭了园门,吃了夜饭,先自上楼睡了。
各房男人,因连夜勤劳了,亦各自分头睡去矣。
倒是元娘,还在那里等茶吃,只见一个女子在那里沏茶。
三才看得停当,去把花园门大开了,将火把只点起两个道:“徐者不必说过。三才领路,某人持火,某人断后。”
计议停当了,悄悄走进那扇门内,一声喊,把元娘一把抱了就走。
刘玉听见吶喊,连忙下楼,家中大小一齐都到,不知什幺缘故,许多人喊下来,一个也不见了。
忙寻元娘﹔并不见影,只见那沏茶的女子掠倒在地。
刘玉忙问,她说道:“许多人拿了刀斧,把娘娘抱去了。”
刘玉惊得面如土色,对众人道:“大家分头去赶。”
一齐往后边赶去。
那伙人飞也的去了,那里去赶得到。
且说三才抱了元娘,恰好城门未闭,元娘不住口中的喊救人,这些家人,都藏过了凶器,路上有人问说因何事故的,回说是逃出来的妇人,路上之人便不管了。
一竟下船,登时摇起三橹。那船如飞的一般去了。
三才把元娘放下,蒋青上前一看,正是元娘,深深作下一揖道:“莫要谅坏了。”
元娘看见是个带巾的一个后生,道:“尊处是何等样人,因甚事抢我到此,有何话说?”
蒋青道:“请娘娘台上坐,容小生告稟。”
一边说,忙去扯一张椅,放在上边。那元娘不肯坐。
蒋道:“小生是蒋青,乃南阳府镇平县人氏。昨日为观花,瞥见娘娘花貌,一夜无眠。至天晚睡去,梦见神人指示,道袁氏与汝有几载风缘,必须如此,方可成就。待缘满之期,好好送回,夫妇重圆。故此冒突娘娘,实由神明托梦。望娘娘应梦大吉。”
元娘道:“做梦乃荒唐之言。岂可读书之人行此强盗所为之事。好好送我回去,我送金帛与你。若不依言,没此河中做鬼,也不相饶。”
蒋青说:“那金帛舍下也有百万,倒不稀罕。若要娘娘这般标致,实然少有。归家藏娘娘千金屋,礼拜如观音,望娘娘俯就。”
说罢取出一盒食撰,一壶三白酒。
那元娘哭将起来,那里肯坐。又没个女人去劝,他心下思量投水而亡,只因身怀六甲,恐绝刘氏宗后,昏昏沈沈,只是痛哭。蒋青没法起来,道:“来了多少路程了?”
回道:“六十余里了。”
“既如此,你们都去睡罢。行船的人,更番便了,大家应了一声,通去睡了,止得二人在船内。
元娘流泪不止,蒋青扯元娘来坐了吃酒。元娘见后边还有舱,竟跑进去,把舱门闭上。
蒋青笑道:“舱门四扇,都可开的,闭他何用。”
他便取了灯火,拿了那壶酒,踢开门来,放在桌上。
又取了那盒儿摆好了,去请元娘。只见袁氏坐在床上大哭,蒋青道:“娘娘,事已至此,你要说我送归,今夜已不及矣。总到家,已做了奇花失色,美玉成暇了。不若依神明之言,了此风缘。那时圆满,送你还家。你夫妇再圆,此为上策。”
元娘道:“难道你家没妻子,别人也这般行凶抢去,完了夙缘,你心下如何!”
蒋青道:“不瞒娘娘说,先室去世三年。因无国色,尚末续弦。今得了娘娘就如得了珍宝一般,与你百年鱼水之欢。”
元娘说:“你方才许我送还,缘何又说百年?”
蒋青说:“若蒙俯就,但凭尊意。”
连忙筛了一大银杯酒,送与元娘。
元娘不理,蒋青又说道:“娘娘,你一来受惊,二来肚己饥下。况酒可散闷。自古将酒待人,终无恶意,吃了这杯。你便饿死在此,家中也无人知道。”
便拿下酒,双膝儿跪将下去。元娘见他如此光景,又恼又怜道:“放在床沿上。”蒋青放下。去取一格火肉,拿在手中,等元娘吃。
元娘只不动,蒋青说:“娘娘不吃,我又跪了。”
言罢,又跪下上。元娘拿上酒杯,哈了一口。
蒋青送上火肉,元娘肚内果然饥了,取了一块来吃。
蒋青道:“求乾了。我才起来。”
元娘无奈,只得吃完了。
蒋青起来,又筛一杯,元娘道:“我吃不得了。不可如此。”
说罢,往枕边一看,见一双女鞋。
元娘道:“你说家中无妻,此物何来?”
蒋青道:“家中便有妻子,带此鞋来何用。这是昨夜神明梦中付我的道:‘若他不信,你可把此鞋与他为証,自然从你,完此姻缘。’你拿到灯下认看。”
元娘拿灯前一看,果是无差。暗忖道:“昨夜那里不寻到,怎幺有这般奇事。”
心下竟有几分信了。
蒋青道:“你如今心下如何?”
元娘遭:“既是前缘,料难过去。我身怀孕二月,在家时,与丈夫便隔绝了此事。待我分娩后,再从你罢。”
蒋青道:“虽不做,同我睡亦不妨。”
元娘不语,蒋青又劝着酒,元娘只得坐下。又吃了一杯酒。
一来空心酒,二来酒力狠,一时头晕起来,坐立不住,连忙到床边,换了鞋儿,和衣睡倒。
蒋青见她说头晕,也知其故,自己斟酒,吃了几杯,想道:“亏我说这一场谎梦,竟自信了。”
心下十分快活,酒兴发了,走到床边,听见元娘鼻息声响,见他朝着床里睡的,推上一推,全然不动,他便携起上边衣服,去解他裙带。
把手衬起了腰,扯下来,露出大红裤儿,真个动兴。
又如前法,露出两只白雪雪的腿儿,一发兴高。
把裙裤放在薰笼里,自己除了巾,脱了衣,放下罗帐,扒在元娘身上,双手推开两腿,将那硬硬的茎儿塞进软软的道儿,云雨起来。
元娘初时睡熟,这阴水一阵阵的流出,便自醒了。口中叹了口气,因下边正在痒的时节,把那些假腔调一些儿也不做出来。
蒋青大喜,索性脱了元娘衣服,弄得赤条条的,元娘道:“且息了灯火来。”
蒋青道:“且慢。”把元娘两腿搁上肩头,着实奉承。
附着耳问道:“可好?”
元娘点头,蒋青吐过舌尖,元娘含住,两个一时间弄得酣美,须臾雨散云收。
蒋青茶炉内取了开水,倾在盆内,净了手。元娘披了衫儿,下床洗刮。
蒋青又扯他吃酒。
元娘道:“吃不得了。”
蒋青笑说:“娘子,让我摸摸你的小脚?”
元娘道:“踩地行路的,有甚可摸。”
蒋青说:“娘子的脚太可爱,不摸摸,心痒痒!”
元娘道:“既已被你沾汙,何有甚幺话说!”
蒋青将元娘双脚捧在怀中,脱去睡鞋,细细玩赏!
元娘问道:“多少年纪?家中还有何人?缘何这般大富?来到安阳县何干?”
蒋青道:“年方二十五岁。家中止有僮仆妇女,共五十余人。祖上收买一乡宦家铜香炉十余个,不料都是金的,变卖了数千金银子,代代传下,渐渐的积将起来。到父亲手内,有了百万之数。固往省下寻亲事,并无标致的,故此转来。偶然看花,见了你姿容,又赐梦兆,果遂良缘。但愿天长地久。”
元娘道:“你如今要我回去,把我怎样看成。”
蒋青道:“是我填房娘子。难道把你做妾不成。”
元娘道:“盖头衣服,并簪钗全无,怎生好到你家。”
蒋青道:“先室衣饰有二十余箱。任凭你受用。到家时,我先取了几件衣服之类,打扮得齐整了,到家便是。”
元娘因不穿下衣的,要去睡,蒋青强他吃了一杯酒,自己又吃尽了盘儿,二人上床后,蒋青又摸小脚,元娘也被撩得兴起,两人重整驾侍,桩捣一番,直至夜分而睡。
且说刘玉在家,着人满城叫了一夜,次早写了几十张招纸,各处遍贴,连寻几日,并无蹤影。
亲朋们纷纷来望,也有置酒解闷的,也有空身来解劝的,这且不提。
再说蒋青船只已到岸口,他使别了元娘,先到家中。
男女见了,道:“新娘到了,快治酒宴。”
一面着人各处请亲友邻居,上楼取了首饰,着小僮拿了, 了一乘四轿同到船边。
蒋青下船,将首饰付与元娘穿戴,不一时,打扮完成上了轿, 至堂上。
两人同拜着和合神,家中男女过来叩首,都称大娘娘。
元娘上楼归房,看了房中,果然整齐,二十四只皮箱,整齐齐两边排着,房中使女四人。
三才的妻子叫名文欢,他原是北京人。这三才原是个北路上响马强盗,后来到了北京,见文欢生得标致,一双小脚,其实可爱,在路上骗他同归寓所,后来事发,官司来拿,他知了风声,与文欢先自走了。
直至镇平县,闻得蒋青是个大财主,夫妻二人靠了他。
蒋青的前妻,极喜文欢,道他又斯文,又欢喜,故此取名文欢,她视元娘如前边主母一般,故此独到房中伏侍,元娘见他小心优待,倒也喜她。
光阴似箭,不觉年终,又是春天。他园中也有百花烂漫,季春也有牡丹,未免睹景恩人,不觉眼中偷泪。又是初夏时,但只见腹中疼痛起来,蒋青分付快请稳婆,须臾已到,恰好瓜熟蒂落,生下一个儿子,眉清目秀,似娘母一般,元娘暗喜。
三朝满月,蒋青竟认为己子,亲友们送长送短,未免置酒答情,不必言矣。
只因元娘产妇末健,蒋青寂寞之甚,常在后园阔步。只见文欢取了一杯茶,送到花园的书房里,放在桌上,叫:“大相公,茶在此。”
说了便走,蒋青见是文欢,叫道:“转来,问你。”
文欢走到书房。蒋青坐下吃茶,问道:“你丈夫回也未曾?”
文欢道:“相公着他到府中买零碎,昨日才去,回时也得五六日,怎生回得快。”
蒋青道:“你主母身子不安。我心中寂寞。你可为我解一解闷。”
文欢脸上红将起来,转身就走。被蒋青扯住,搂了亲嘴。
文欢低头不肯,蒋青叫道:“乖乖,我一向要与你如此。不得个便宜,趁今日无人在此,不可推却。”
文欢道:“恐有人来,看见不便。晚上在房中等相公便了。”
蒋青笑说:“也好,但现在要让我摸摸你的小脚?”
文欢斜睨了一眼道:“须快!莫被人见了!”
蒋青将文欢抱在怀中,不去摸脚,却来摸乳,将个文欢逗得吃吃笑道:“你如此调戏,奴家下面尽湿,须去换裤,你且放了,今夜任你要煎要煮就是!”
蒋青放了手道:“不可忘了。”
文欢笑嘻嘻的去了。
只见到晚,蒋青在元娘面前说:“今晚有一朋友请我,有夜戏。恐不能回了。与你说一声,元娘说:“请便。”
蒋青假意换了一件新衣,假装吃酒腔调,竟自下楼,悄悄走到三才房门首,只见房里有灯的,把房门推一下,拴上的,把指弹了一下,文欢听见,轻轻开了。
蒋青走进房中一看,房儿虽小,倒也清洁有趣。
文欢拴上房门,拿了灯火,进了第二透房里。见卧床罗帐,不减自己的香房。
蒋青大喜,去了新服,除下头巾。只见文欢摆下几盒精品,拿着一壶花露酒儿,筛在一个金杯之内,请蒋青吃。
蒋青道:“看你不出,那里来这一对金杯。文欢道:“还有成对儿哩。”
蒋青道:“你有几对?当时不来靠我了。”
文欢将三才为盗,前后事情,对他一说。蒋青说:“难怪前番抢元娘一事,这般有胆。”
二人坐在一处。蒋青把文欢抱在身上,坐着吃。
文欢道:“你再停会快进去。恐大娘娘寻。”
蒋将前事一说,文欢笑道:“怪道着了新衣出来。”
蒋青看了文欢说笑,动了兴,把文欢拦腰抱到床上。但见她罗裙半卸,绣履双挑。眼朦胧而纤手牢勾,腰闪烁而灵犀紧凑。
蒋青喜不胜收,将文欢衣裳尽脱,寸褛不留,妇人芳兴甚浓,春怀正炽,亲扶玉杵入臼,是以玉容无主,任教蹈碎花香。弱体难禁,持取番开桃浪。
那文欢兴动了,她是北方人、极有淫声的,一弄起,便叫出许多妙语来。
须臾,两人住手,文欢去取水,洗了一番,收捡桌上东西,与蒋青脱衣而睡。
摸摸肉足,抚抚酥胸,未免又撩云拨雨起来。
自此,蒋青常常托故,把三才使了出去,便来如此。
文欢见三才粗俗,也不喜他,故此两人十分相好。
不觉光阴似箭,那刘玉个小娃子,长成六岁,元娘主意,取名蒋本刘。
恰好一日蒋青不在,有一算命的人,叫做李星,惯在河南各府大人家算命的,是蒋青一个朋友荐他来算命的人元娘听见,说:“先生,把本刘小八字一算。”
李星道:“这个八字,在母腹中,便要离祖。后来享福.况富贵不可言。”
完了,又将蒋青八字说了。李星道:“此贵造,也是富贵双全,只是一件,子息上少,寿不长些。”
元娘把刘玉八字念了,李星道:“这个贵造,倒像在那里算过的了。待我想。”
元娘道:“既如此,你且先把女命来排一排看。”
说出自己的时辰八字。李星打一算,把手在案上一拍道:“是了,是了,这两个八字,在安阳县里刘相公府上算来。这女命有十年歪运。死也死得过的。若不生离,必然难逃。幸喜他为人慈善,留得这条性命。缘何府上与他推算?”
元娘道:“你几时在他家算来?”
李星道:“今年二月内又算过了。那男命也不好,行了败运,前年娶了一个姓猪的妻房,又是个犯八败的命。一进门,把个使女打死了,被他父亲定要偿命,告在官府。府官明知他是个财主,起了他二千两银子,方才罢手,一应使用,费了三千两。不曾过几时,他房中失了火,把屋字烧个精光。房中细软,尽百人抢得罄尽。”
元娘道:“这般好苦。”哭将起来。李星道:“还好。”
元娘注了泪道:“有何好处。”李星道:“他速把山地产业尽情变卖,重新造屋,复置物件。不期过得一年,这犯八败的命极準,又是一场天火,这回弄得精光。连这些家人小子也没处寻饭吃,都走散了。”
元娘又哭起来。李星道:“还好。”
元娘止住哭道:“什幺好处?李星道:“没甚幺好。我见你哭起来,故如此说。”
元娘道:“如今何以栖身?”
李星道:“我今年二月,在一个什幺袁家里算的命,说是他岳丈家里。”
元娘道:“这个人后来还得好幺?”李星说:“这个命目下就该好了。只是后妻的命不好,累他苦到这般田地。还有一个那妇女的命,目下犯了丧门绝禄,只怕要死。死了,这刘先生便依先富了。”
元娘道:“先生几时又去?”李星道:“下半年。”
元娘道:“我欲烦先生寄封信去与他。若先生就肯行,当奉白金五两。”
李星听见一个五两,道:“我就去,我就去。”
元娘叫文欢取了纸笔,上写:“妻遭茶毒手,不能生翅而飞。奈何。不可言者,儿郎六岁矣。君今多遭艰难。”
正写着,报到官人回了。元娘把纸来折过了,便进内房,添上“书不尽言,可即问李星十寄书的所在。你可早来,有话讲,速速。袁氏寄。”
即胡乱封好,取了五两银子,着文欢悄悄拿出去,与他寄去,不可遗忘。
文欢寂寂的,不与蒋青知道,付与李星道:“瞒主人的,你可速去。
李星急急出了门,往安阳地方而去。
不只一日,到了县中。他一竟的走到袁家,见了刘玉道:“镇平县里一个令亲,我在他家算命,特特托我寄一封书来与你。”
刘玉茫然不知。拆开一看,见是元娘笔迹,掉下泪来道:“先生,他在镇平县什幺人家?”
李星道:“本县第一个财主。在三都内蒋村地方。主人蒋青,是个监生。”
刘玉想道:“是强盗劫去,买与他家的了。”
又问道:“寄书的,是怎生打扮?”
先生道:“她躲在屏后讲话,并不见面,声口倒似贵县乡音一般。蒙他送我五两银子,特特寄来的。”
刘玉想道:“有五两银子与捎书的,他倒是好生在那里了。可藉没有盘费,去见得他一面方好。
李星道:“别了。”
刘玉道:“因先室没了,茶也没人奉得。”
李星听说没了,道:“好了,好了。那个女命,向来不可在你面前讲得。是犯八败的。死得好,死得好,你的造化到了。”
刘玉道:“造化二字,没一毫想头。”
李星道:“镇平令亲,有百万之富。你若肯去,有一场小富贵,决不有误的。”
刘玉道:“奈无盘费。妻父家中,因亡妻过世,又累了他,不敢再启齿得。如之奈何?”
李星道:“不难,不难。蒙令亲见赐五两,一毫末动。我取二两藉你,到下半年,我若来,还我便罢。”
连忙往袖中取出,恰好二两,一定称过的,递与刘玉。刘玉道谢不已。
李星去了。刘玉与岳父母把前事一说,袁家夫妻道:“好了。幸喜女孩儿还在。贤婿,你去打听,仔细通知了浑家。见景生情,不可造次。”
袁家取了一副舖陈,五两银子,一个小便,并女儿小时的一个香囊把与刘玉。登时别了,一路而来。非止一日。
到了蒋村,天已晚了。寻一客店安下。次早梳洗,穿了店家,指示了蒋家大门。
刘玉着小使拿丁香囊道:“你只管走进去,若有人问你,你说安阳县袁相公来望元娘娘。切不可说是我刘字起。”
小使说:“这些不须分付。”
一直走了进去。
恰好这日蒋青往乡间去了,不在家。故此没人在家中答应。小使走到堂后,恰好见一标致妇人,便拜了一个揖道:“烦劳说一声,安阳袁相公,来望元娘娘。”
文欢晓得原故,忙往楼上叫道:“大娘娘,你快下来。”
大娘见说,一径下楼。只见小使叫声亲娘。元娘一看,便哭起来。
“大官人特来望着亲娘。”小使把香囊与元娘一看,元娘道:“陕请进来。”
文欢忙忙走出前厅,把手一招,刘玉走进厅前。
文欢道:“请相公里边来。”
元娘迎将出来,两下远远望见,都便硬咽。见了礼,二人哭做一堆。女仆便都道是兄妹,只有文欢晓得是夫妻。因元娘待文欢如妹子一般,文欢感激不尽,又蒋青偷他一事,元娘也知,并不妒他,故此亦不与蒋青说寄书事起,这是两好合一好的故事。
元娘住泪,请了刘玉往楼上坐了,将前情说个透撤道:“我正然早早寻死,固有孩儿,是你的骨血,恐绝了你的宗支。今己六岁了。”
刘玉道:“如今在那里?”元娘道:“在书房里。”
刘玉道:“取名唤叫什幺?”
元娘道:“名字是我取的,叫做蒋本刘。”
正说穿,文欢抱上楼道:“小叔来了。”
本刘朝着刘玉作上一个揖。刘五看见他生得眉清目秀,心下欢喜。
元娘请丈夫坐了,附着耳道:“明日我将些金银与你,拿到店家藏了,陆续运到几千两,叫了船只,暗暗约了日子,带了孩儿逃回乡。不可吐露。”
刘玉喜道:“若得贤妻如此,方见本心。”
两人吃了酒,文欢收了,打发使女下楼去睡着。奶娘领小官去睡。元娘拴上房门,去取锁链,开了个金银箱道:“趁蒋青不在,将来结束了,好日逐取去。”
一包一包的缚了半夜,约有几千两,珠翠金宝,不计其数。都停当了,身子通倦,夫妻二人就枕,刘玉楼了元娘,便求云雨。
元娘替玉郎宽衣解带,然后褪去下裳,仰卧床边,任其抽弄。
元娘道:“玉郎,奴家已失身于人,你不弃嫌?”
刘玉说:“娘子情深义重,更令人倍觉可爱!”
元娘道:“然则已生个孩儿,一定宽松了。”
刘玉说:“娘子旧时常叫痛不 ,现时正出入自如哩!”
两人恩爱一番,双双睡去。
次日早早起来打点,袖了出门。小使身边也带几百。一日几次而走,店家那里知道。
不须三日,通运完了。
刘玉与元娘道:“物己运完,我想人无远虑,必有近优。承说一齐逃去,我想船重行迟,倘被他人家一齐赶上,那时你我性命难保。连孩儿也不能活。若我与小使先回,到了家中,将银子即造起房屋,置物件,般般停当,那时我再来望你。早晚相机而行,空身好不便捷。只有一件,恐一时取起金银不见了,叫你如何存济?”
元娘道:“这夹楼板内,都是金银。但钉好的不便取出来。那银子日逐只有得此起,再无有动用内囊的。若要时,只管取去不妨。”
刘玉道:“我方才这番说话,你意下如何?”
元娘道:“你说的是万全之计,只是不知你几时方来?”
刘玉道:“多只在明年。”
元娘流着泪道:“我度日如年。你休忘了。”
刘玉道:“事不宜迟,就此去罢。”
元娘道:“整酒来,与相公送行。”
元娘又去取了一双金镯,两双金簪道:“你谅情寄与爹爹、母亲。哥嫂之处,不可太重,亦不可太轻。”
吃罢了酒,别了元娘,两下流泪。
小使取了舖陈,一家大小,送出门外。
刘玉竟至店家,送了房金,觅船回去。一路幸喜平安。
回到袁家,说了前话,送了袁家二十两银子,便去买起木料,又整新居。
正是钱可通神,有了银子,又是那般富贵起来了。
将田地产业,尽行赎取,不在话下。
且说蒋青,故意着三才出去,又与文欢取乐。
不期一日正与文欢两个睡着,天色尚末明,便又高兴起来。
谁知三才搭了夜船回家,握城门面进,竟至家中,叫开了大门,竟往回廊下,取路走到自己房内,把手推门,门竟汤开了。
三才想:“倒为何门开在此?”
只听得房内响,轻轻的走到床横一听,只听得“这样好幺?”
文欢道:“好。”
淫声叫得好不发兴,三才听了大怒,往皮靴内取出尖刀,摸着蒋青一把头发,竟把头割。
喉咙已断,跌在一边,去模文欢,竟不见影,他想道:“莫要被他走了。”
急去拴好房门,寻着灯火,点得亮亮的,内外一照,那里见影?
急急往外去看,门上人说不曾见人出来。又往后边,见内门都开了,问着女使道:
“可见我娘子幺?”
使女回道:“不见。”
他往内边又寻,直至主人内楼,见房门闭好,恐惊动了主人,想道:“被好了,自古捉奸见双,走了淫妇,杀了这人,到官必要偿命了。”
后到房中道:“不知奸夫是谁?”
把灯去照,叫声:“苦也!别人还不打紧,擅杀家主,要碎剐零卸的。怎幺好?”
想道:“收捡了金银,趁早去罢。”
打开箱子,取了金银子,正待要走,被尸首一纠,跌了一交,浑身是血。
间壁伙伴听见跌响,还睡在床中,只道有贼,便鸣了两声。
三才听见,一发急了。
要走时浑身是血,一时情急,便道:“我往时杀了多少人,这一死也该的。”
拿着尖刀,往喉咙割,扑地跌倒。
众家人齐听见响得古怪,大家走到房中一看,只见两个死尸倒在地。
登时喊到内房,元娘听见了道:“为什幺大惊小怪?”
原来这文欢见三才行凶,急下床扯了衣服,竟至内边敲开房门,与元娘说他行凶。
元娘见事已至此,着文欢拴上房门,穿好衣服,伴在楼上。
见下边乱嚷,开了房门,只见众家人报:“大娘娘不好了,官人杀死在三才房内,三才也被杀死在地。”
元娘吃惊道:“文欢,你房内杀死了主人,快同我去看来。”
元娘与文欢三脚两步,竟至外边,见了尸首,关将起来。
文欢倚了三才尸首,也哭起来,众人道:“不知何故,双双杀死在此。”
元娘见一大包在地,提一提甚重,教人拿在桌上,解开一看,道:“是了,是了,是我房中失去金银,恐官人埋怨,不敢明言,恰被官人知道。三才盗去,今天早官人道过,趁三才不在,文欢又在此睡着,他取灯火,竟来搜出赃物。想道凶手偶回,见事露了,把家主杀死。正待收捡这包物件要走,恐怕被人捉住,一时情急,自刎而亡。”
大家一看道:“大娘说得一些也不差。果然是自刎的。”
元娘道:“文欢之罪难逃矣。这金银岂不是你盗去与他的。必要经官究罪。”
众人道:“求大娘娘饶恕了。他如今他丈夫已死,是个孤妇子,正好陪侍大娘。”
说罢,一齐跪下。元娘心下正要假脱,连道:“若不看众人分上,决不饶你。”
即时分付众人,查点各箱笼,共五只与我槓了进去。”
着人看着尸首,忙忙进内,分付把总的管家,要一付上好抄板,买一付五两棺木,打点一应丧仪,把三才盛贮了,先始到城外埋了。
把主人尸首洗净,唤人缝好,下了棺木,拾上中堂,诵经礼仟,讣音上写蒋本刘做了孝子。
那此亲眷都来吊奠。
过了七七,出了灵枢,元娘把内外男女,都加恩惠,逢时遇节,俱赏金银,无一人不感激着他。
文欢竟在元娘房中住下,把那里死人房屋拆去一空地。
看看过了百日,又将过年,正在那里想,刘玉恰好到了。
刘玉听见蒋青已死,先着人买了祭奠之礼,方进堂来灵前祭奠。
本刘回礼,进内见了元娘,夫妻二人又悲又喜。
元娘道:“官人别后可好幺?”
刘玉把家门重整之事,细说一番,元娘欢喜道:“此间百万家私,皆是我的了。如今末可便回。待孩儿长大,娶了妻室与他。那时和你归家方是。”
刘玉道:“贤妻见教不差。我想上天有眼,蒋青起心拆我夫妻,岂非天报乎。”
元娘道:“三才之自刎,亦是天报。”
刘玉不知其故,元娘把平生为盗,后来抢掳元娘情由一说,刘玉道:村皇天有眼。”
文欢又整了酒,送上楼来。元娘道:“此妇即三才之妻,为人文雅,你可收他做了二房。”
文欢听见,娇羞掩面竟自下楼。
刘玉道:“不可。”
元娘道:“若是如此,只我和你有归家之日。不然一去,谁人料理家务?”
刘玉这才点头。
晚间,元娘就推刘玉去文欢睡房,并为两人掩门而出,文欢知刘玉心有顾忌,便亲为卸衣,主动奉迎。
那文欢是一经行房就要叫床的,一抽两插,早淫呼起来。
元娘推门进入,骂道:“死文欢,大娘让了你,你却如此叫嚣,要收回丈夫了!”
文欢抱住刘玉腰身,说道:“大娘!此刻你杀了我也不放了!”
元娘道:“浪蹄子,不要面了!”
文欢道:“大娘!此刻下面爽得紧,那顾得要上面了!”
元娘道:“骚狐狸,不与你理论了!”
元娘说罢,转身要出去,那文欢其实是知情识趣,故造气氛,见元娘要走,连忙推开玉郎,赤身裸体追至,把元娘宽衣解带,脱个精光,推入玉郎怀抱。
刘玉此刻左拥右抱,一时抽抽元娘,一会插插文欢,早几年所失,今已加倍得偿。
这刘玉从此也不归家,合家人都知刘玉是丈夫,因元娘加恩,都不敢多言。
本刘十六岁,中了乡科。明春联捷,娶了本处王尚书之女为妻,复了本姓,唤名刘本,刘玉夫妻同了刘本夫妻往自己家中拜见亲友。
刘本夫妇重到蒋村,奉文欢如已母,后至京师,二母皆有封赠。
后来刘本把房屋田地买与大户,将什家伙送与妻家,取了金宝细软之物,尽底先送到父母处,带了夫人并庶母,别了岳父母,竟至本乡,奉侍父母天年。
元娘笑道:“好奇,又月开花是一奇,打动女人是二奇,梦中取鞋是三奇,蒋青之报是四奇,三才自刎是五奇,反得厚资是六奇。”
刘玉笑道:“分明陈平六出奇计。”
夫妻大笑。正是: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 终 –
男人不识本站,上遍色站也枉然
秘密入口
开元棋牌
PG娱乐城
永利娱乐城
棋牌游戏
澳门葡京
新葡京
PG大赢家
开元棋牌
官方葡京
澳门葡京
新葡京
PG大满贯
开元棋牌
威尼斯人
PG娱乐城
开元棋牌
澳门葡京
太阳城
PG娱乐城
澳门葡京
PG国际
开元棋牌
威尼斯人
大发娱乐
英皇娱乐
官方开元
呦呦破解
免费呦呦游戏
少女·网红·破处
反差女神外流
萝莉直播大秀
黑丝人妻NTR